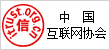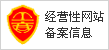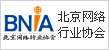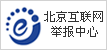“弱势群体”变了,伪善者的虚伪和残忍没变
2021-11-20 09:35:02
骑士影院在线看最热影视 https://www.qishi.run
伪善者总是在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时,“善意”满满、近乎肉麻。让别人付出代价的“善意”,他们更是亢奋得惊天动地。要是能“因善之名”挥舞大棒,那更是皆大欢喜、普大喜奔的欢乐场景。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关不羽
讲一件小事。
那不过是朋友圈里转发的一张图,上不了热搜、成不了头条,却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01
一个在读大学生在校友圈里发了一篇个人经历的长文,说他骑自行车看电影,和一位外卖小哥出了个车祸。学生的自行车坏了,外卖小哥更倒霉,外卖包飞出去了,还受了点伤。
外卖小哥要他赔100元,学生还到了50元。外卖小哥接受了, 还感慨了一句“行吧行吧,反正我们生来就是不同命的”。
这让他深受感触,字里行间充满了歉意和同情,最后提醒大家注意骑行安全。
看得出这是一个率真、善良的年轻人,文字朴实而坦诚。
但是,他的坦诚善良,换来的却是谩骂。 在一片谩骂声中,他删帖并申请销号,但是自以为善良的人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他的某位校友把截图放到了豆瓣的一个小组,还给出了义正辞严的结论,“只赔了50元,发到校友圈还觉得自己好善良”。结果又是新一轮围攻。我没有看到任何人为他辩解。
在我看来,这是一群自以为善良的人,伤害了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自以为善良”。
02
如果这场小事故是学生之间发生的,充其量也就是“骑车注意安全”而已。竟然把他从校内骂到校外,无非是涉及到了外卖小哥。
涉及到“弱势群体”的话题上,自以为善良的人士在总会在第一时间炸毛。条件反射的速度和准确度,堪比巴甫洛夫的狗狗闻到了北京烤鸭的味道。
至于那位委屈巴拉的外卖小哥,只存在于背景墙上。 那群“自以为善良”的人无一提出联系他、为他提供一些帮助——那应该很容易做到,但是他们忙于用谩骂秀自己的善良,顾不上真正的善举。
这是一场道德A货的表演,让人恶心。
03
道德A货从不关心真实的个体,他们打着“弱势群体”的旗号,其实只是抽象的符号。
清洁工可能是弱势群体符号化的最早版本,给我留下了印象最为深刻。
在我的学生时代,每年五一劳动节,都要被教育“劳动最光荣”,清洁工总是被歌颂的对象,奉上“城市美容师”之类的美名。
过不了几天的五四青年节,又是另一种励志教育。备受推崇的是科学家、工程师之类“祖国需要的人才”,从来没人教育我要当“城市美容师”,难道是祖国不需要他们?
至于日常生活中,“学习不好就去扫大街”,是老师和家长的“教育箴言”。 符号的含义随着场景切换,天差地别,众人安之若素。
后来农民工接班清洁工,成为新一代“弱势群体符号”,情形也差不多。
他们继承了劳动节礼遇规格,再加上背井离乡的境遇,还会在春节、中秋节被多歌颂扬几天。但是,照例,“祖国需要的人才”的名单里也不会出现他们,更没有人会鼓励自家的娃立志成为农民工。
“教育箴言”改成了“学习不好,将来到工地和农民工一起搬砖”,也是私下的小声嘀咕,在一本正经的公开场合决口不提。
上海曾经出过一首宣传歌曲,歌颂农民工之余,还提了一些城市生活的建议,诸如注意个人卫生之类的。对符号公然的“大不敬”当然被骂得一塌糊涂,那首并不高明、用心不坏的宣传曲歌很快销声匿迹、灰飞烟灭。
但是,“农民工的汗是都香的”之类的肉麻话喧嚣一时,改变不了什么。假装农民工和香妃一样香汗淋漓,可不会为狭窄拥挤的宿舍增加卫浴设施,也不会减少公交车上的白眼和嫌弃。
歌颂之后,一切如常。
04
互联网舆论开始接棒符号事业,“保护弱势群体”就成了烽火连天的光景。
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了活靶子。 曾经轰动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最让人印象深刻,不管社会学家的统计数字,还是心理学家对自杀成因阻的分析,都阻挡不了互联网上“保护弱势群体”的巨大热情。
结果却是诡异。
一面是互联网上富士康工厂堪比集中营般惨绝人寰的绘声绘色;另一面却是富士康招工现场的火爆场景。最终当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全面胜利,富士康工厂北迁了。
▲ 图 /图虫创意
我不知道那些等待招工的农民工会怎么想。后来听一位干过富士康的“弱势群体”说起往事,“辛苦是辛苦,但是赚得到钱”,“要不是厂关了,谁来干这苦差事”——他在搬家公司再就业,并不顺心。
别的“血汗工厂”当然更惨,连搬家的机会也没有,就地躺平。 再后来,“血汗工厂”称谓几近消失,客客气气地称之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么就是大而化之的“实体经济”。
这几年总有一些奇怪的新闻,比如中国人偷渡到越南,只是为了在中国人开的工厂里打工。
“保护弱势群体”的胜利,算是弱势群体的胜利么?
05
然后,轮到了外卖小哥的符号化。
外卖小哥成了被“保护”的符号,要比前辈们丰富多彩。 “血汗工厂”的土味惊悚,变成了“困在系统里”的IT感十足。控诉的声浪一波压过一波,“算法”之恶、资本之恶,头头是道。
但是,并不见差评减少、小费增加,更没有人欢迎涨价。
系统之外还有系统,系统也受困在系统里。困住系统的系统,顶点是符号化的外卖小哥,最底层的则是外卖小哥本尊和其他更弱势的群体。中间的一大票“自以为善良”的,忙着寻找加害的对象。
多年以来,符号变来变去,虚伪没有变,更多了几分残忍。
▲图/图虫创意
2017年,一段凉山少年铁笼打拳的视频在网上传播。 一时之间,组织孩子们的拳击俱乐部被千夫所指,“用孩子牟利”的指控铺天盖地。“热心志愿者”的奔走“帮助”下,那些孩子被强行带走,塞回了家乡。
可是,现场并没有孩子们被“解救”的欢声笑语,而是“我不想回去”的哀鸣。至此,才有人关注事件的真相。
一位参军离开家乡的退伍军人,开设了一 家拳击俱乐部,把家乡的孤儿接来,和他一样改变卑微的命运。
没有奴役孩子的大魔王,只有一技傍身、吃穿不愁的朴素道理。这不符合“保护弱势群体”的审美需求——读书改变命运可以有,打拳改变命运就不行。
三年后的2020年,当初喊着“我不想回去”的少年成了全国冠军。鲜花和掌声献给了伟大的事业,顺便也成了“志愿者”们的功劳。 但是,没有人提起当年给孩子们拳击梦想的那个老兵,没有赞扬,也没有迟到的道歉。
那位年轻的冠军在采访中说,如果专业道路走不通,就成为一名拳击教练,回家乡办个拳击队,小孩子们就不用外出学拳了。
我挺为他担心,担心那些爱心人士、志愿者还在暗中窥伺。
以“弱势群体”之名,他们寻找敌人,用来宣泄他们的恶意。
06
“敌人”总是不缺,就像那位不幸和外卖小哥撞车的年轻人,一起事故,一人社死。
我不知道校友圈里的大批判会对这个年轻学子造成多大影响,大学的校园不大,很快就会暴露身份。我不知道那些自以为善良的人会不会在他背后小声嘀咕、指指戳戳;我不知道沦为同龄人的猎物,会有多么痛苦。
这场风波,多半会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份纯真的善良。
善意得不到善意的回应,真诚反思却让自己陷入了众矢之的的境遇,那个成为“敌人”的学生是否还能保持善良、坦诚?但愿会,但这真的很难。心灵的创伤,很难被治愈。
善良的最大敌人不是邪恶,而是伪善。邪恶的狂风只会摧折善良的枝叶,伪善的毒素却会摧毁对善良的信心。
伪善者总是在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时,“善意”满满、近乎肉麻。让别人付出代价的“善意”,他们更是亢奋得惊天动地。要是能“因善之名”挥舞大棒,那更是皆大欢喜、普大喜奔的欢乐场景。
我们的舆论场就这么成了道德的粉碎机,填进去一个又一个善良的灵魂。
至于弱势群体,依旧在神坛上永生,在生活中失声。听任那些自以为善良的人士,按照想象的剧本为他们“改变命运”。但是,弱势群体的命运从未因为他们的剧本变好一点点。
清洁工依旧卑微,农民工慢慢变老,外卖小哥还在为差评烦恼。也许他们应该庆幸没有变得更糟,比如那些跑到越南打工的人、那些被塞回家乡的孩子。
是时候问一下,何谓善良?是平等博爱之类的宏大叙事,还是“老吾老及于人之老”的朴素小事?比如,连自己的校友同学都不能善待,还谈何善良?
*题图为外卖小哥(图/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