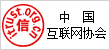女兵浴:七十年代,西藏女兵的洗澡问题
2021-10-04 16:09:40
女兵浴
——献给曾经的高原女兵
王素彬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妩媚的阳光让成都平原的油菜花开出了一片灿烂。柔弱的花朵,摇曳着纤细的腰身,微风里舞动着战士般的军姿,整齐一致地向左,向右。
此时的我们,即将开拔高原的新兵连队,紧锣密鼓做着进藏的准备。
我突然发现从什么时候,连队的领导总爱站在驻地的小溪旁,对着那片油菜开出的花海指指点点。赏花?观景?都不对啊,三个月的摸爬滚打,严格的军事训练把我们修理的疲惫不堪,早已丧失了赏月观花的雅兴,何况这些资深的老兵呢。
奇怪,猜疑不得而知,直到几个怪模怪样的东西被抬了过来,哇,拌桶,老百姓打谷子用的拌桶,用厚厚的木头做成上宽下窄的梯形,下面有一底板。丰收的季节,它被抬到田间,一面用竹席遮挡,一面站人,用力将稻谷在拌桶沿摔打,用这种最笨重,最简陋的原始方法来实现稻与谷的分离。
哦,明白了,领导是想让它代替澡盆让我们洗澡。
洗澡?想到我们青春如花的身体,要在这个黑黢黢,笨重又古老的拌桶里洗去灰尘,女兵笑倒一片。
四个月没有洗澡了,是没有地方洗。七十年代,洗澡需要去街上的澡堂。我们训练的小镇离县城二十里地,新兵连没有车,就是有车县城也没有能装下二百多个女兵大池子啊。
此时我们明白了领导的用意,用拌桶洗澡确属无奈,在训练中绝不手软的领导,到了离别的时候,还是想让年轻的女兵干干净净的走进西藏。
剩下的时间,拌桶静静地躺在溪水里,缝隙被棉花密密地填塞,壁上的污垢被细细地打磨,期待水流的滋润将岁月留下的粗砺,裂痕,软润光滑。
几天后,小溪边搭起一溜绿色的帐篷,拌桶被抬了进去,挖灶立锅点火,临时军用浴室开张,四人一组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水一倒进桶里,我们发现高估了棉花的作用,原来的缝隙变成了瀑布,水流的稀里哗啦,于是不停的掂水,烧水,倒水变成繁忙的工作。
因为烧火我最后进去,帐篷里已变得泥泞不堪,手拧着鞋不知道何处能下脚,小心翼翼迈进了拌桶,只觉脚下极滑,一个踉跄跌进桶里。呵呵,桶壁不用水来滋润,油垢就能把它润滑了。
好不容易洗了个澡,感觉应该是不错吧,其实不然,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皮肤已经习惯与灰垢的融合,现在硬将它们分离,皮肤不适应了,它让宿舍充满抓挠声,一屋人被骚痒折腾的辗转反侧,一夜难寝。
进藏后分到通信总站,“一号命令”的下达,通信总站跟随军区各部搬到自治区委。电话连分配到山脚下年份已久的藏居,生活条件简陋,即便是冬天也没有热水供应,日常生活用水是露天的一个水管,水至山上引下。夏天还好,冬天呢?在西藏寒风凛冽的冬天,十五,六岁的我们还是有些畏惧,最冷的时候我只保证脸和手的干净。
一次,到军区总医院检查时需要验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护士,用酒精棉球擦拭胳膊,几个棉球下去发现皮肤还是干干的。小护士感到奇怪,把棉球看了看说可能是太干了,你等着,我再换一瓶。瞬间我就明白了不是棉球干,是我胳膊太脏了。棉球里含的那点酒精根本无法穿透皮肤外的“保护层”。
趁小护士离开,我急忙跑到水管边,用最快的动作把胳膊进行了清理。也就是打那时候起,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再艰苦的地方,只要能搞到水,哪怕是冰冷的水,也要将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
搬回军区洗澡方便了,大院的浴室是太阳能,西藏充足的热能资源保证从中午对我们开放,我们每个星期至少可以洗上一次。
麻烦也来了,军区大院那么多的女兵,就这么一个澡堂,人拥挤的时候就像现代版的公交车。其实挤来挤去最多的是总站和文工团的女兵,这两个女兵最多的单位相互间还瞧不上,她们在我们眼里是矫情,得瑟。我们呢?在她们心目是什么不得而知,但从瞟过我们的眼神中答案不会好了。
每次洗澡都要抢,抢房间啊。回回都是总站女兵嘻嘻哈哈抢先冲进,并迅速在房间挂上挎包(嘿嘿,占山为王)。其实“抢”对我们就像玩耍中的游戏,尽管是“抢”,还是自觉的两人合用一间,要给后进人留下足够的房间。
一天中午,我和刘技师,董金宁下班后去洗澡,在等候的时间,发现今天的文工团女兵有点怪,离门口远远的,大门开了也不往前。
我们笑逐颜开去抢占房间,进去后发现是有些不对,第一间,第二间,以后的几间全部都有挎包,直到最后一间才是空的,没有办法,按照规矩今天我们三人合用一间。本来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各洗各的,随后各走各的。
有这种事不嫌大好事者。隔壁屋突然传来嗲嗲的川普话:“好安逸哦,今天小张又帮我占了一个位置,还是洗单间”。哇塞,谁这么张狂跑到这里走后门(那个时候走后门是被鄙视的)?刘技师一把没有抓住,我跑了出去,只见房门虚掩,那位说话嗲嗲的女兵背对我冲刷着什么。一人独占一间真的好得意,自在与兴奋随水汽在空间漫延。她愉快地哼着小调像在挑衅,又像是炫耀,我的脾气彻底爆了,冲进去一把抓她的衣领使劲往外一推,刚才还哼着的小调瞬间变成了尖叫,我顺手将把她的挎包抛出,随着“砰”的关门声,外面的尖叫此刻变成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
当然走后门现象依然存在,不过那嗲嗲的炫耀声再也没有出现。
总不能每次洗澡都是这样抢来抢去的,我们开始选择了新的位置。贸总对面有个地方办的浴室,屋里面积不小,一溜床,一溜隔成小间的淋浴室,就是条件太差,床铺上除了几块光秃秃的板子,再就是我们的挎包了。
浴池的服务员是位藏族老太太,每次见到我们总是连说带比划嚷嚷半天,听不懂,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感觉与水有关系。
不知道他们这里用的水是烧的还是太阳能的,冷,热交替频率变化无常,就像在坐过山车。常常是洗着洗着,一声尖叫我们被水烫得跳了出来,要不就是我们被凉水激得抱着膀子在一旁打哆嗦,任凭你叫喊,敲管子,刚才还在喋喋不休的服务员此刻已不见了踪影。
时间长了得出经验,水最好的时候只有几分钟,进去身体打湿后肥皂立马跟上,搓揉片刻迅速冲洗速战速决。如果今天的水好就再慢慢享用,水不好穿衣服走人。
也有不灵的时候,一次,我和慧莲进去肥皂沫还没有冲完,水就没有了,呼喊,敲打任何原始的联络方式都试完,外面没有一丝动静,仿佛瞬间空间只剩我们两个。
不知道喊叫多久,远远传来军区的午休起床号,归队的时间到了,看着这一身的肥皂沫,再看看依然不会流水的淋浴头,我们恨得咬牙切齿。
回到连队,还没有找到哪里有水把头发打整一下,去工区劳动的车已经发动。那天的劳动真的郁闷死了,毒辣的太阳,将汗水和残余的肥皂沫搅和在一起,又黏又滑,又扎又痒又无处挠,身体嘛还有衣服遮挡,头发呢,那没有洗尽的头发呢,尽管被严严地塞进帽子里,但心里总不踏实,提心吊胆的害怕汗水会不会让肥皂沫变成泡泡会从帽子下边飘出来。
多少年过去,多少年后我们又见到彼此,我们依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心大笑,在笑声里,隔着岁月经年我仿佛又看见火热军营里那年轻的笑容,还有穿过生命中你,我的青春。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王素彬1969年12月成都入伍。西藏军区通信总站电话连战士。1976年退伍。定居河南,从事通信行业至退休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