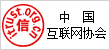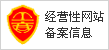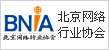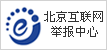深圳,凭什么是酒类包装设计“第一城”?
2021-09-21 15:41:02
去往甲古文的路上,我们被本地的滴滴司机半路“甩客”了。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小山坡后,实在找不到剩下的路,导航却显示,甲古文就在附近100米处。
我们决定下车步行,果然,峰回路转。
在路尽头的铁栏杆旁,有一条窄窄的人行小路。顺着这条路走不到3分钟,能看到一栋3层高的小别墅,这就是甲古文的工作室——据说这里曾是深圳最早的一批别墅,产权还归属袁庚曾创立的蛇口招商局。
在工作室的身后,是蛇口招商局船厂码头的员工宿舍,楼房的外墙皮已有些脱落,露出了斑驳的灰色水泥,而1公里之外就是蛇口港。
初到这里,你会因一种时空的反差而稍有恍惚——这一面是年轻无极限的创意和时尚,另一面却写满了历史的足迹和风霜。
放眼中国酒类包装设计,有两个重要的聚集地。一是成都,一是深圳。
成都,因背靠川酒而占据先天优势。名酒众多,厚重历史和文化底蕴,对设计者而言,犹如一座珍宝无数满目琳琅的殿堂。
因此,这里更有机会出大师,万宇、许燎源都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深圳则是另一条路径。
去年刚过完40岁生日的深圳,是一座年轻而鲜活的城市。
作为中国的经济前沿和对外门户之一,这里汇聚了世界上最时尚的潮流趋势和大量的新兴产业。
从这里走出来的腾讯,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交方式。华为更是从这里走向全球,为中国制造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深圳与酒的关联也透着现代意味。这里鲜有知名的酒企,却因为超强的消费能力,成为众多品牌的必争之地。
这里还是中国酒的“颜值担当”。无论是白酒、啤酒还是葡萄酒,在许多我们曾为之眼前一亮的产品背后,都有着强大的深圳设计基因。
从产业的角度看,深圳当之无愧是中国酒类包装设计的“第一城”。那么,为什么是深圳?
一座被“设计”出来的城市
1979年的深圳,还只是一座人口不足3万的小渔村。
从昔日的“深水沟”到后来的国际大都市,深圳的纵身一跃,始于蛇口。
▲ 蛇口集装箱码头
1978年,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被委派到香港,担任招商局的主要领导。赴任当年,香港招商局要建后勤服务基地,由于地价太贵,便选择了与香港仅隔一条河道的广东省宝安县(深圳前身)。
经过考察,他们相中了蛇口,向中央提出在这里划出一块地作为工业用地。随后这里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为了吸引外资,袁庚在权限范围内一再简化各项流程,使蛇口工业区成为外资蜂拥而入的栖身地。以蛇口为前沿,世界上最先进、最潮流的东西,先后汇集到深圳,再从这里走向中国的其他角落。
▲ 深圳河两侧,分别是深圳的高楼大厦和香港的水稻农田
作为一座被“设计”出来的城市,深圳特区建立初期,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承接了来自香港等地的大量加工业务。靠着这种贸易形式,早期的深圳淘得“第一桶金”,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进程。
位于深圳罗湖区与福田区交界位置的八卦岭工业区,是深圳最早的大型工业区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厂房林立,数以万计的打工者,身着厂服穿梭其间,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包装印刷厂。
这一时期,由于许多香港印刷企业内迁,以及日本、美国等地企业纷纷前来投资设厂,大量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涌入,让深圳印刷业异军突起,且在起步阶段就跨越“铅与火”,直接进入“光与电”时代。
当时在印刷业,流传着一句“全国印刷看广东,广东印刷看深圳”。高峰时期,曾有上千家印刷公司云集于八卦岭,并且形成了平面设计、器材供应、纸品供应等供应链完整的印刷产业集群。
▲ 位于蛇口的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到本世纪初前后,短短20年时间,深圳已成为与北京、上海鼎立的全国三大印刷基地之一,尤其擅长高端印刷。
印刷产业的发达和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运用,为深圳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土壤。当时有全国各地的设计人才,怀揣着梦想来到深圳,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为中国设计界的金字招牌。
北京奥运会申奥标志的设计者陈绍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 陈绍华
在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第五届主席孔森的印象里,90年代初期深圳设计师的作品,在中央电视台的出镜频率很高,“就我个人而言,每天晚上都能看见自己起码3~4件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这些从深圳走出来的设计作品中,不乏酒类产品的身影。不过,在这一时期,酒水行业尚未形成清晰的品牌意识,大部分酒厂对于设计的需求还相对简单。
如果酒企想做一款新包装或形象设计,通常不是对接设计公司,而是直接找印刷厂。所谓设计,只是承接生产附带的免费服务。
直到1999年前后,在大约1400公里之外的成都,因川酒“六朵金花”在高端品牌打造上率先起势,进而相继涌现出水井坊、国窖1573、舍得等一批经典产品时,深圳也在同一时期,开启了酒类包装设计的专业化运作。
从洋河的蓝色到老窖的高光
赵国祥第一次和客户谈产品设计费的时候,对方以为他疯了。
那是在1999年。尽管当时深圳已经有300多家包装设计公司,但并没有专门针对酒水行业的。在深圳打拼多年的赵国义、赵国祥兄弟,从中看到了机会,于是主打酒类包装设计的柏星龙,在这一年创立。
创业初期一没背景,二没资金,“靠的都是一帮‘小孩’”。
出生于1974年的赵国祥当时也很年轻。他记得那年第一次参加在大连举办的糖酒会时,连个成品样都没有。所谓的样品,就是用喷墨打印机将设计稿打印出来,然后由所有设计和销售人员自己动手裁剪而成。
▲深圳柏星龙创意包装执行总裁 赵国祥
就是靠着这些半成品,还有公司提出的“打造新奇特的产品包装”创意理念,柏星龙在这届糖酒会上打开了局面。
柏星龙收到的第一笔设计费是5000元,来自河南的一家酒厂,这在那个年代已是不小的数字。也是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酒企才明白,原来包装是有“设计”的,而设计是有价值的。
不过,真正让赵国祥感受到设计的巨大价值,还是洋河蓝色经典的“偶然”诞生。
2002年洋河找到柏星龙时,最初的诉求只是想打造一款形象产品。
这一年的洋河其实已走到背水一战的关口。时任洋河市场部部长张学谦提出,“一款形象产品是挽救不了企业的”,于是建议开发一套系列,既有形象产品,也有市场主推产品。
在最初起名字时,赵国祥提议叫“蓝色风暴”,洋河高层则认为太过激进,坚持叫“洋河大曲”。后来也是张学谦建议,取一个“蓝色”、一个“洋河”,再加一个“经典”,洋河蓝色经典由此而生。
当时为了这个项目,赵国祥曾一年飞到洋河9趟。在他看来,洋河蓝色经典也是柏星龙最经典的一个案例。
2003年洋河蓝色经典上市后,迅速从市场上普遍主打红色的产品中脱颖而出。
由于顺应了消费者审美和口感的变化,又正好赶上了中国白酒一路高涨的黄金十年,洋河在市场上掀起了一场真正的蓝色风暴。甚至超越泸州老窖成为行业三甲,奠定了白酒江湖持续至今的“茅五洋”三足鼎立格局。
彼时身为柏星龙设计总监的刘文,也是洋河蓝色经典的设计主创。
他认为,好的设计语言一定是基于品牌本身。第一代洋河蓝色经典的“创新”,其实是继承了洋河大曲的独特美学基因,即美人瓶和蝴蝶标,还有经典的蓝色。
时至今日,洋河蓝色经典已经迎来5.0版本,伴随着手工班、梦6+等产品的推出,蓝色视觉始终被保留了下来。
近年来另一款具有强烈符号化色彩的白酒作品,是去年10月24日上市的泸州老窖高光。
以极光绿作为主色调,将不同波长的光线,以斐波那契螺旋线的黄金分割美学组合成闪耀光芒。极简而极具质感的设计,让人很容易忘记它其实是一款光瓶酒。
或者说,高光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光瓶酒的传统形象认知。
高光的设计团队,是刘文后来创立的甲古文。
▲深圳甲古文创意董事长兼首席创意官 刘文
从去年3月19日确定高光项目,到4月8日提案,4月18日打样生产,整个设计过程只用了1个月时间,然而这款产品早从2017年就开始酝酿。
所谓“高光”,从物质层面理解是高档光瓶酒,精神层面则是“人生高光时刻”。于是,刘文选择用“光”来诠释高光。
▲高光设计手稿
人用肉眼能看到的可见光波长约为380~760nm,即只有这个范围内的光能刺激到我们的眼睛,产生视觉。正常视力的人对555nm的光波最为敏感,而这段光波正处于光谱中的绿光区域。
在刘文看来,高光不是普通的高档光瓶酒,而是重新定义了中国白酒,
“就像2700美金一公斤的冠军咖啡豆,1粒豆子就值6块钱。高光也是要用小杯喝的酒。”他还尝试在自己的酒吧里用高光调了很多鸡尾酒,据说很受欢迎。
“设计不仅仅是设计本身,而是从战略出发,要改变消费业态才更有价值。”刘文说。
无论是洋河蓝色经典还是高光,都在包装设计中表现出了对消费趋势的引领,这两款产品也几乎贯穿了深圳酒类设计的20年。
为什么这些极具变革精神的产品设计,都诞生在深圳?
“设计之都”的启示
从1997年开始做设计,1999年担任设计总监,刘文在深圳设计圈已经打拼了24年。在他看来,深圳设计跟成都的很大不同,在于对商业价值的理解。
“全中国开咖啡馆唯一能赚钱的就是成都”,刘文说,在成都开公司的成本相对较低,生活也安逸,因此成都的设计大多很文化,偏重对传统的挖掘。
深圳则惯于颠覆传统,并且对商业趋势极为关注。
“不同的土壤,塑造了设计师的两个江湖。”
在洋河蓝色经典和高光之外,牛栏山经典二锅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16年、一坛好酒·红坛、雪花匠心营造、马尔斯绿、李渡窖龄等一大批经典产品的包装,也先后出自深圳设计师之手。
刘文在2019年重新设计了梦之蓝M6的升级产品M6+,这一年刚好也是梦之蓝系列上市10周年。
作为一款升级产品,需要一些符号来告知和引导消费者,就像苹果手机会有PLUS版,刘文则提出了一个“+”的概念。
所谓“+”,意味着更大更多更好,于是M6+的容量由500ml变成550ml,瓶子更好看,酒体中的老酒也更多。
而消费者通过一个“+”,可以迅速建立对产品升级的认知和互动,甚至不需要去做消费者教育。
在刘文看来,这就是商业设计的意义。“商业设计师”,也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和标签。
柏星龙对商业的理解,则是基于市场。
赵国祥认为,商业设计有别于艺术创作,是靠市场来孵化的。他会要求设计师“不能在办公室里,而要在市场一线进行产品设计”。
正是因为洋河蓝色经典的大获成功,让柏星龙改变了对设计的认知,从原先纯粹的包装设计公司,转型为注重品牌建设。后来在做设计之前,柏星龙的创意团队,都会先对产品市场深入调研,将一手数据融入产品策略中,并最终通过创意落地。
截至2019年底,柏星龙的调研团队已经走过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1200多个县市,6000多个乡镇,走访过的销售终端超过27000家,在全国累计开展过1200多场消费者座谈会。
而成立于2013年的凌云创意,从创立之初,就提出一个理念:设计负责打中,营销负责打穿。
▲凌云创意创始人兼首席创意官 邓雄波
作为凌云创意的创始人兼首席创意官,邓雄波一直认为视觉美感从来都只是基本前提,要达到设计的商业目的,还需要考量设计师对品牌的理解,对市场的感知,甚至是对消费者人性的捕捉。
在柏星龙、甲古文、凌云之外,深圳还活跃着一大批与酒业相关的设计公司,比如潘虎、古一、飞人谷、黑马奔腾等。
他们中有些以创意设计见长,有些产品开发能力较强,有些主打品牌全案输出,有些定位于设计生产一条龙,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高度重视设计的商业价值。
这也是深圳设计的特质。在深圳,几乎是不存在艺术与商业之辩的,反而能看到二者结合的无限可能。
▲甲古文和深圳华侨城联合创立的潮流共生空间
2008年,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中国第一个、全球第六个“设计之都”。
当时给出的评语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城市,(深圳)有着很短却充满活力的历史,以及年轻的人口,令人印象深刻。由于本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深圳在设计产业方面拥有巩固的地位。它鲜活的平面设计和工业设计部门,快速发展的数字内容和在线互动设计,以及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环保方案的包装设计,均享有特别的声誉。”
目前深圳还在打造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深圳创意馆,建成后不仅将是深圳的新地标之一,还将成为世界级的设计朝圣之地。
作为“设计之都”的一部分,酒类设计也承袭了深圳设计的基因和产业基础。这里可能没有名酒和大师,却有着世界顶尖的设计产业链条和创新环境,以及源源不断的人才。
“来了都是深圳人”
对于深圳这座被“设计”出来的城市而言,人是一切的起点。
作为中国现代化设计的发轫之地,深圳曾聚集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设计师。
文章开头提到过袁庚开发蛇口的故事,如今虽然走过了40年,当年的某些场景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去往甲古文的路上,我们被本地的滴滴司机半路“甩客”了。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小山坡后,实在找不到剩下的路,导航却显示,甲古文就在附近100米处。
我们决定下车步行,果然,峰回路转。
在路尽头的铁栏杆旁,有一条窄窄的人行小路。顺着这条路走不到3分钟,能看到一栋3层高的小别墅,这就是甲古文的工作室——据说这里曾是深圳最早的一批别墅,产权还归属于袁庚曾创立的蛇口招商局。
在工作室的身后,是蛇口招商局船厂码头的员工宿舍,楼房的外墙皮已有些脱落,露出了斑驳的灰色水泥,而1公里之外就是蛇口港。
初到这里,你会因一种时空的反差而稍有恍惚——这一面是年轻无极限的创意和时尚,另一面却写满了历史的足迹和风霜。
甲古文每年开年会,都会有不同主题的员工大合影。2013年的合影背景,就是这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码头船厂员工宿舍。
那一年,甲古文已经在业内建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刘文去企业提案的时候,不用再反复介绍甲古文,他就是最好的代言人。
也是这一年的一个夜晚,在深圳罗湖向西村的一家店名都有些模糊的鸡煲店里,几个年轻人围桌而坐,畅想着他们刚刚成立的设计公司今后的发展。
开业初期的第一单,是广东惠州的一家米酒企业。去提案的那天,正好赶上台风。车子走在大雨滂沱的盘山公路上,几个人提心吊胆,邓雄波还有些晕车。
到了之后,企业对设计很满意,老板直接让助理从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拿出一沓钱。这是凌云创意收到的第一笔设计费,1万块。
就是在这样一个像极了港片的场景里,凌云开张了。
2019年,柏星龙成立20周年庆典时,曾邀请了公司早期发展的一些见证者,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是洋河股份总裁助理、江苏双沟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张学谦。
赵国祥还曾想要找到当年给柏星龙支付第一笔设计费的那家河南企业,可惜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时间也太过久远。
当年他们兄弟从黑龙江来到深圳时,正是深圳缺人的年代。不管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学历,只要你能有勇气从家乡走出来,这个城市都会包容。
“在深圳打拼的这些企业家们,每个人要是回忆起来,都是一段辛酸史。”
不过直到今天,赵国祥说自己依然非常喜欢深圳,就因为这里的包容,还有鼓励创业的营商环境。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设计之都”的背后,也是“创客之城”。
如今,深圳已经成为中国设计人才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拥有39600多家创意设计企业,从业人员大约12万人。
他们可能是湖南人、江西人或是四川人,但来了深圳后就都成了“深圳人”。
尽管来到这里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正是这些怀揣创意和梦想的年轻人,让深圳这座“设计之都”的边界不断被拓宽,也由此缔造了酒类包装设计的“第一城”。
参考文献:
《梁湘、袁庚、任正非……深圳简史》 关思滢
《印刷界三分天下:揭开深圳印刷业的崛起之谜》
《世纪初深圳最大的印刷市场——福田八卦岭》